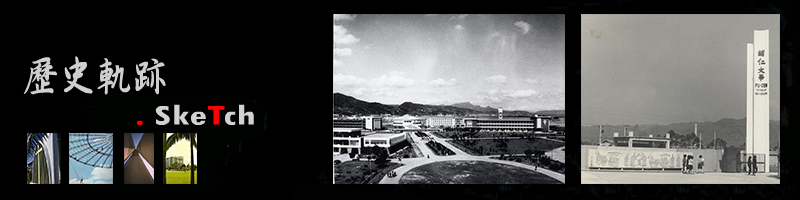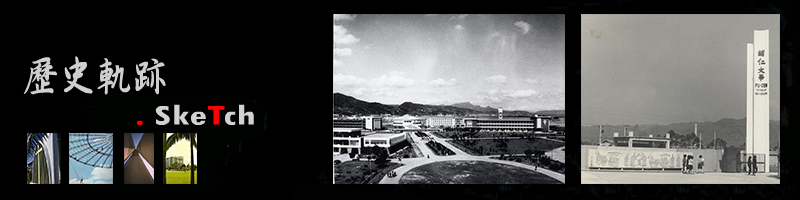|
陳方中
一般人總把天主教在十九世紀三度傳入中國,視為是鴉片戰爭的影響。典型的說法是,傳教士是乘著軍艦大砲進入中國。不過就本質而言,十九世紀的傳教活動,是與鴉片戰爭沒有直接關聯的,道理很簡單,傳教活動是在鴉片戰爭以前恢復的。
禮儀之爭以後,雍正開始禁止天主教傳播,於是進入了所謂「禁教時期」。有人喜歡說康熙晚年禁教,不過我認為重點不是某些諭旨中禁教的話語,重點是實際上康熙並未採取禁教的完全措施,他只是命令不願「領票」的傳教士離開。這個禁教時期歷經雍正、乾隆、嘉慶、道光,嚴格來說,到咸豐十年才完全結束。此前,因為鴉片戰爭,中英訂定了南京條約:法國不甘示弱,也在道光二十四年和中國簽訂了「黃埔條約」,以及其後要求道光皇帝降下諭旨,證明天主教是勸人為善的好宗教,並非左道邪教。這是天主教與一個所謂帝國主義國家拉上線的開始。
但是中國政府禁教,只是傳教活動減少的其中一個因素,甚至可以說是較次要的因素,引起傳教活動減少,真正重要的因素來自歐洲,這個因素就是─法國大革命。廣義的法國大革命可從一七八九年開始說起,直到拿破崙徹底失敗的一八一四年為止。當時一些活躍的傳教團體,如遣使會及巴黎外方傳教會,都接近停止活動的狀態。耶穌會相對來說還較幸運,因為他們早在一七七三年就廢止了。法國大革命影響所及不只法國而已,全歐洲都在其風暴中,方濟各會及道明會的傳教主力雖不僅只法國,但也受到極大的影響。教廷當時也代表整個天主教會,處於一種極端困難的狀態;因此之故,一八二○年以前,全中國平均起來,各傳教團體的所有外籍傳教士總共也不過只有十位左右。在這段期間已有數倍於此的國籍神職,但他們通常只扮演助手的角色。
法國大革命結束以後,遣使會、耶穌會及巴黎外方教傳教會都恢復活動。十九世紀是一個與前面數世紀截然不同的年代-宗教自由,宗教容忍逐漸形成一種歐洲價值,天主教信仰不再是唯一的正統,即使是天主教信徒也認知到信仰是多元選項之一。但經過選擇後的信仰活力更大、熱忱更富,因此一八二○年後,巴黎外方傳教會逐漸增加他們派往四川的傳教士,這些傳教士在轉往雲貴、西藏、東北、高麗。在一八四○年以前,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人數已有十三人,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多,但已超過十七、十八世紀的任一時代;遣使會也在一八二九年開始回到中國,一八四○年前,他們的人數也已達到空前的高峰。
耶穌會士的確是在一八四○年以後才回到中國的,但耶穌會早在一八三○年代就開始策劃。他們的問題是已將在中國的傳教區讓給了遣使會,而遣使會當然不願將北京再交給耶穌會;另一個問題是耶穌會士當時堅守不擔任主教的誓願,因此必須等到南京主教畢學源逝世以後,與耶穌會友善的傳信部傳教士羅伯濟被教廷派任山東代牧主教,並因毗鄰的關係,署理南京教區,耶穌會才有機會進入江南傳教,而這時正是鴉片戰爭爆發以後。
方濟各會當時傳教規模略遜於前述三個團體,但也在一八四○年前恢復了他們的晉陜湖廣的傳教工作。既然這些團體都在一八四○年前開始了他們往中國的傳教工作,或至少開始籌劃,那當然就不能說他們是在鴉片戰爭後,乘著軍艦大砲回到中國的。
另一方面,我們也必須承認,鴉片戰爭帶給傳教活動一定程度影響。首先是開放的口岸,傳教士開始在上海、寧波等開放給外國人的港口及其附近區域展開公開傳教活動,法國領事已可在這些港口施加其影響力,但是超出口岸影響的範圍,實際上仍是秘密傳教的。其次是傳教士也逐漸感受到其母國,尤其是法國,可在中國政府不遵守條約的情形下,做為他們向中國政府爭取權益的靠山。不過,傳教士對其母國政府的態度也不一致。因為歐洲各國政府在十九世紀,也不乏各種反天主教的措施。因此,比較公允的說法是,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,而在此之前已經恢復的傳教活動,也在這種新的關係中發展。
由此而產生了一個問題: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錯誤的概念?我認為原因有三。第一,我們對中國天主教的歷史缺乏了解;第二,我們受民族情感的影響把現象視為原因;第三,我們從未從宗教本質看傳教活動,反而過度看重政治對宗教的影響。而這三點將是未來論述的核心。
| Back
|
|